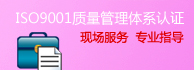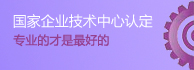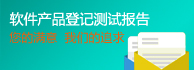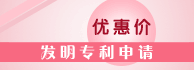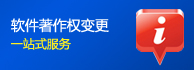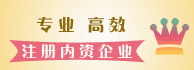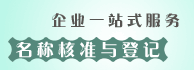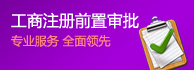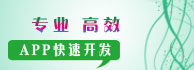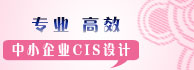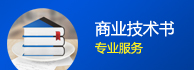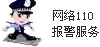微信文章
曾国藩如何评价日本?应对之道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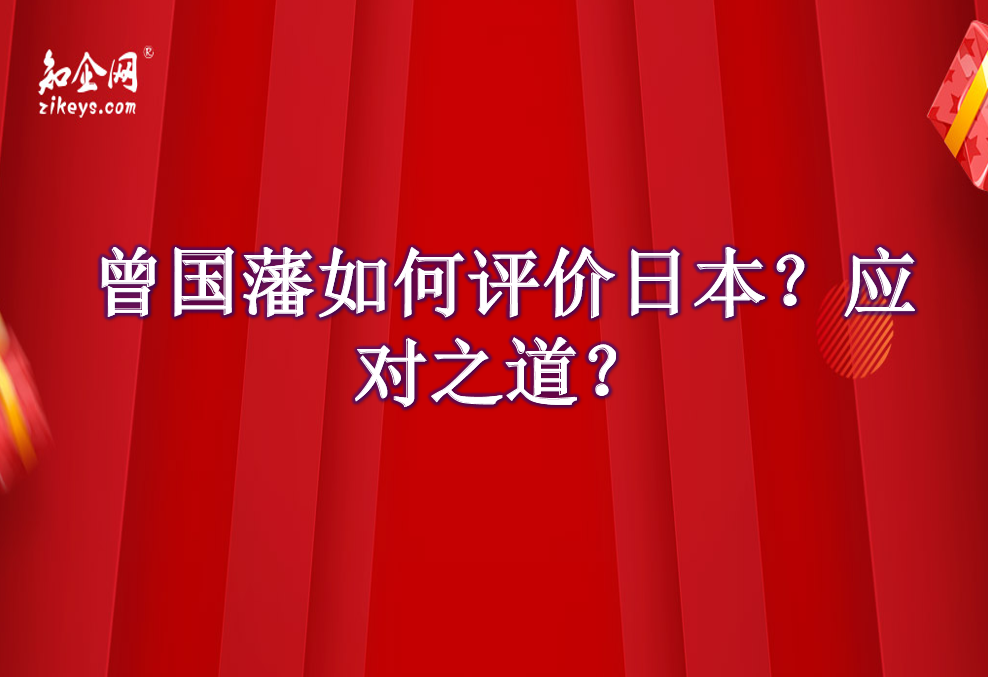
在晚清“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,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先驱与清廷核心重臣,以超越时代的战略眼光洞察到日本的崛起之势与潜在威胁。他对日本的认识并非停留在传统华夷之辨的桎梏,而是基于地缘格局、变革本质与国家实力的理性判断,形成了“正视变革、警惕野心、自强应对”的完整认知体系,其远见在二十余年后的甲午战争中得到深刻印证。
曾国藩对日本的关注始于对“近忧远患”的地缘敏感。19世纪60年代,当清廷上下仍将英法等西洋列强视为主要威胁时,他已通过《日本外史》的研读与边报信息,注意到这个一衣带水邻国的异动。历史上倭寇侵扰东南的教训,让他对日本“桀黠嗜利”的品性留有深刻印象,而1853年佩里叩关后日本出现的变革迹象,更让他敏锐察觉到潜在危机。同治六年(1867年),他在与幕僚赵烈文的闲谈中直言“大清未来之患在日本”,彼时明治维新尚在酝酿,这一预判堪称超越时代的洞见。与赵烈文“或为盗窃而已”的轻估不同,曾国藩的判断建立在对日本民族性的深刻认知之上——他评价日本“看似虚心学习他国,实则内心龌龊,外表谦恭,内则十分诡诈残暴”,这种对其“畏威而不怀德”本质的洞察,与左宗棠“知小礼而无大义”的评价不谋而合。
面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全面变革,曾国藩突破了传统官僚的盲目自大,以务实态度承认其变革成效与潜在实力。当清廷多数官员嘲笑日本仿行西法为“东施效颦”时,他已通过驻日使臣奏报与洋商反馈,看清日本“举国求变”的决心:“岁入虽仅我十一,然六成用于练兵造船,每岁添置兵船不下二三艘”。他清醒认识到,日本的学习并非表面模仿,而是“欲彻底重塑国力根基”的全面革新,这与清廷洋务运动“中体西用”的局部改良形成本质区别。1870年日本使节柳原前光访华请求通商时,清廷高层多主张拒绝,曾国藩却在《复陈日本通商事宜折》中提出“彼国援西国之例,诣阙陈辞,其理甚顺”,既承认日本已非昔日“蛮夷小国”的现实,又坚持“不载比照泰西总例一语”,警惕其借西方规则谋取“利益均沾”的野心,展现了正视对等与防患未然的双重考量。
基于对日本威胁的深刻认知,曾国藩将“自强”作为应对核心,把海防建设与造船工业视为关键抓手。早在1861年创设安庆内军械所时,他便特意命人试制蒸汽轮船,开启大清自主造船的尝试。1865年,他整合资源成立江南制造总局,明确将“制造轮船”列为核心要务,派容闳赴美国采购先进机器,并亲自拟定《局规》,要求“造船需按西洋最新形制,选材必求坚密,工艺必求精细”。1868年“恬吉”号兵轮试航时,已身患眼疾、左目几近失明的曾国藩亲往吴淞口检阅,在日记中感慨“大清自强之道,或基于此”。他深知,应对日本的觊觎,绝非空谈主战或妥协求和所能奏效,唯有“内修政事,外练强兵”,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海疆。在与文祥的书信中,他进一步明确战略重点:“朝鲜为我东藩,琉球为海上屏障,倭人若据有此二地,则我之海疆门户洞开”,因此力主优先加强台湾、澎湖等地的海防部署。
曾国藩的应对策略始终秉持“以自强为根本,以和谈为权宜”的务实原则。他反对盲目主战,认为晚清国力衰弱,应利用和谈争取改革时间,但强调“和谈不可无底线,必须以保全领土为前提”;同时也坚决反对一味主和,痛斥清廷“海军经费岁拨不过百万,且多有挪用”的弊端,反复呼吁朝廷重视实业与军备。遗憾的是,由于清廷体制僵化、官场推诿扯皮,他的诸多主张未能完全落地,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经费多次被克扣挪用,自主研发进程受阻。即便如此,他创办的军工企业与倡导的海防理念,仍为晚清海军建设奠定了基础,其“日本学西法而强,我亦当学西法而更胜之”的自强思想,也成为后世洋务运动的核心指引。
曾国藩对日本的认知,本质上是一位传统士大夫在民族危机面前的理性觉醒。他跳出了华夷之辨的文化偏见,以“强国竞争”的视角看待日本的崛起,其核心逻辑“正视差距—警惕威胁—自强破局”,既不同于顽固派的盲目自大,也区别于投降派的妥协退让。尽管受时代局限,他未能触及政治制度层面的改革,但这份超越二十余年的战略远见与脚踏实地的自强实践,不仅展现了晚清务实派官僚的担当,更为后世留下了“安内必先攘外,自强方能安邦”的深刻启示。

上一篇文章:
已经是第一篇了!
下一篇文章:
墨痕载道:曾国藩书法里的坚持与通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