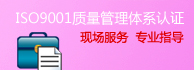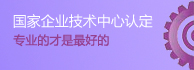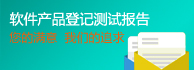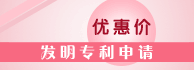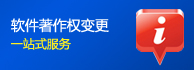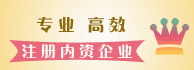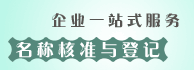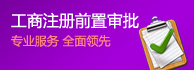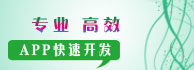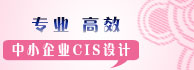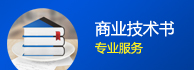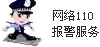微信文章
笔墨根脉:从日本书道申遗反观中华文化传承之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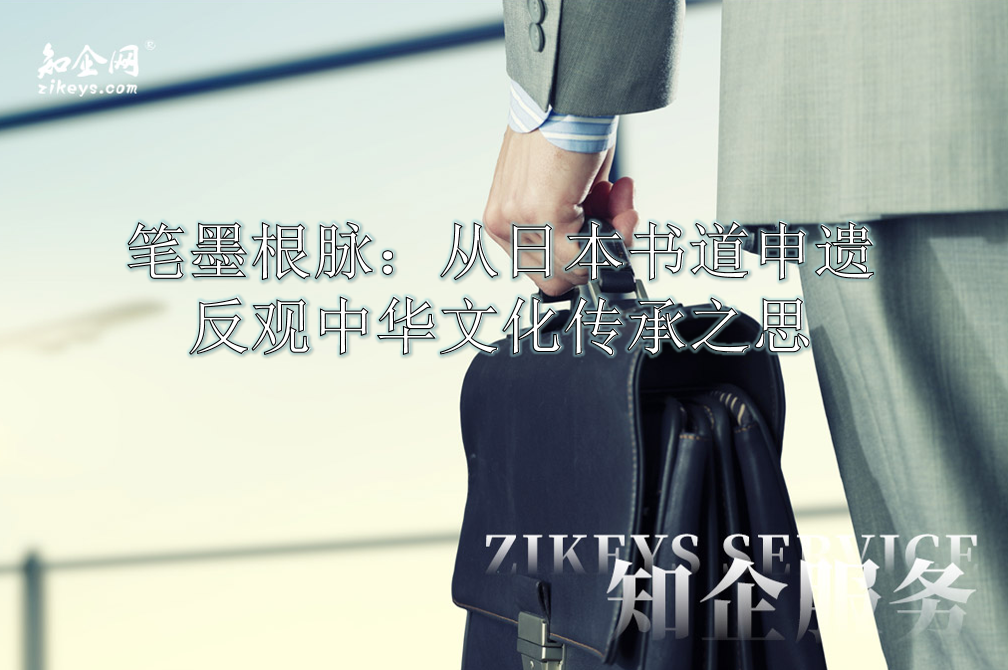
近日日本将“书道”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候选对象的消息,在国内引发广泛讨论。不少人发出诘问:作为汉字书法的策源地,我们为何要面对这样的文化场景?这场热议与其说是对他国申遗行为的争议,不如说是对中华文化传承现状的深刻警醒。
首先需要厘清的是,中国书法早已于2009年9月30日正式列入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 。当年,中国书法家协会与中国书法院历经近五年筹备,克服申报文本严苛、跨文化解读困难等诸多挑战,最终以承载三千年文化积淀的书法艺术打动国际评委[__LINK_ICON]。日本此次申报的“书道”,虽源于中国书法,却在漫长发展中融入其民族特质,成为独特的文化表达——这恰印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“活态传承”的特性,即文化在传播中会因地域与民族特质产生新形态。但这丝毫不能消解一个事实:汉字是中华民族的创造,书法艺术的哲学内核、技法体系与文化基因,始终根植于中华大地。
回望历史,日本在千百年间对中华文化的学习与吸纳有目共睹,从建筑形制到茶道礼仪,从典籍文本到笔墨艺术,无不留有中华文化的深刻印记。然而近代以来,其转向西方的发展路径与历史上对亚洲邻国的伤害,更让我们意识到:文化传承的中断与异化,可能带来何等深远的影响。而今日本对“书道”的申遗重视,与我国传统文化曾面临的传承困境形成鲜明对照——工业文明浪潮下,钢笔取代毛笔,键盘消解笔墨,电子书让宣纸蒙尘;白话运动虽推动教育普及,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言文与现代生活的割裂;简体字的推行提升了书写效率,但也使部分人与繁体字承载的文化密码渐行渐远。当我们的孩子对古籍中的繁体字感到陌生,当年轻人难以体会文言文的韵律之美,文化传承的断层便已悄然出现。
值得欣慰的是,文化传承的火种从未熄灭。教育部早已将书法教育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,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明确要求,从小学低年级的基本字书写到初中的行楷练习,书法教育需贯穿始终[__LINK_ICON]。北京等地的中小学将书法纳入学分考核,湖南、河南等省份通过“国培计划”累计培训数千名书法骨干教师,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更上线了全学段书法教学资源,这些举措正在为传承夯实基础。国学平台的兴起、传统节庆的复兴,也彰显着文化自信的回归。 但文化传承绝非简单的“复古”,更不是形式上的复刻。恢复繁体字与文言文,不应是对简体字与白话文的否定——要知道简体字大多源自历代已有的简化写法,本就是汉字发展的自然结果;文言文的价值在于其凝练的表达与文化承载,更适合在国学教育、文献研究等领域传承。真正的传承,是让书法成为涵养心性的日常,而非单纯的技能考核;是让传统服饰的美学融入现代设计,而非刻板的复古穿戴;是让古籍中的智慧启迪当下生活,而非束之高阁的故纸堆。
日本书道申遗带来的不是文化危机,而是反思契机。汉字书法从甲骨文的刻痕到兰亭序的风流,从颜筋柳骨的端庄到狂草的恣意,承载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审美追求。作为文化源头,我们的使命不在于纠结他人如何传承,而在于构建系统化的传承体系:让书法教育走进更多课堂,让古籍解读触达更多大众,让传统艺术与现代生活深度交融。
笔墨当随时代,根脉必须坚守。当孩子们握起毛笔体悟“力透纸背”的力道,当年轻人能读懂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意蕴,当传统文化真正成为生活的一部分,我们便无需担忧文化根脉的失落。这,才是对书法申遗最好的回应,更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底气所在。

上一篇文章:
以忧立家,以素传芳——曾国藩家风中的生存智慧
下一篇文章:
祁门困守:洪家大屋的戎马文心与战略抉择